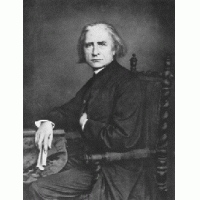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音乐
道教音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它与其它宗教的音乐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用音乐来渲染和加强宗教仪式的气氛, “赞”、“颂”采用庄严而有节奏缓慢的旋律以及吸收民间音乐素材的创作方法等方面,都十分相似,这都是宗教音乐共性的表现。
但是,由于道教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道教音乐势必受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特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状况、民众的欣赏习惯、道教的教义和宗教仪式结构等的制约,因此,道教音乐必然会产生与其它宗教音乐完全不同的情况,显示出中国的民族宗教音乐的明显个性。道教音乐的个性 ——即客观存在的种种中国特点,是构成道教音乐区别于其它宗教音乐的内在原因。也只是对于道教音乐的形成,以及它在形式上、结构上、创作方法上、在宗教仪式中的运用上的种种不同于其它宗教音乐的特点,充分地进行研究,才可能对道教音乐在我国音乐艺术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世界宗教艺术中的地位作出恰如其份的估价。
一九六零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杨荫浏先生在一次关于宗教音乐的演讲中,谈到过道教音乐。他认为,西欧宗教长期与政治直接结合,教会控制国家、控制音乐和文化,因此,宗教音乐是由教会控制的、雇用的专业作曲家创作出来,而道教音乐的情况则不同。他说: “中国宗教音乐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日积月累,逐步由集体加工而成”,所以,道教音乐的形成和发展,“经常受到广大人民美学观点的支配”,它“拒绝不了民间现实主义的强大影响”,道教音乐在形成和发展上的这种中国特点,正是它能够汇集中国历代民间音乐的重要原因。仅就这一点来说,道教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关系,从古代至近代,都是十分密切和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情况,在西洋宗教音乐中是没有的”。杨荫浏先生这一关于道教音乐特点的论述,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道教音乐特点的核心。可惜的是杨先生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想就道教音乐的演唱和演奏、和宗教仪式的关系、和民间音乐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作些说明。
在演唱和演奏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诵唱是由信徒或歌唱家组成的唱诗班担任,管风琴、钢琴则由教会聘用音乐演奏家担任。近世基督教,由一般信众所唱的诗歌逐渐增多,甚至成为礼拜仪式的重要组成部份。还有象神剧 (Oratorio)、宗教清唱剧(Church cantata)等都是宗教音乐,但是它的演唱和演奏都是由音乐家担任,而不是由神职人员来演出的。总之,在宗教音乐的演唱、演奏上,神职人员不需要有超过一般信众的能力。但是,与此不同,道教音乐的诵唱和乐器演奏均由道士、即职业的宗教徒(相当于天主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担任。在斋醮仪式中,信众在极个别法事中虽然也参与小部份活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跟在法师、道士后面跑跑“龙套”,但是,他们并不参加诵唱和演奏道教音乐的活动,更多的是作为观众和欣赏者在一旁观看和聆听。道教音乐完全由道士演奏、演唱的特点,就要求道士不但要熟悉道教经卷,精通斋醮仪式,而且还要有演唱道曲、演奏乐器、吟袭(类似戏曲念白的宗教念白)、禹步(类似午蹈的步法)等等的艺术的本领。随着历史发展,对于一个道士应有的艺术水平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所以,江南民间流传一句谚语说:“出一个秀才容易,出一个佳(能干)道士难”,就是说,一个道士不但要学会宗教的一套,而且在演唱、演奏上也要有较好的艺术水平,只有在唱、念、做、演奏乐器等艺术方面才能出众的道士,才有资格在斋醮法事中担任“都讲”、“高功”等较高的职务。因此,在道士学道过程中,正一派道士从小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习艺,这种习艺从教授的形式到学习的内容,几乎和近代戏曲科班的学习相差无几。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南方诸省和江南一带正一派道士,实际上大都具有初级的艺术水平。而且在一大群具有初级艺术水平的道士中还不断产生一些著名的音乐家。中国现代南北派琵琶演奏大师,如上海的卫仲乐先生,已故的孙裕德先生和北派的李延松先生,这三人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同一位演奏家汪煜庭先生的门生。汪煜庭是一位艺术水平很高的道士。又如著名的民间音乐家阿炳,他的《二泉映月》是家喻户晓的名曲,他从童年至三十岁左右,都是无锡雷尊殿的道士,他的艺术生涯中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是从事道教音乐,从艺术学习的规律上来看,这位艺术家曾经受过二十余年的道教音乐的熏陶,道教音乐要求道士演奏、演唱的特点,使阿炳打好了“童子功”的艺术功底。此外,道士的鼓和笛子的演奏功夫,在各地民族器乐演奏者中,一直享有较高的评价。全国解放后,各地在筹建民族音乐演奏团体和戏剧团体的时候,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进入各种艺术团体,很快地胜任了艺术工作。这种情况不正是道教音乐的演唱演奏特点的一种反映吗?
在音乐和宗教仪式的关系上,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中,读经、讲道和唱诗这几个内容,并无情节上的串连,音乐的运用是为了创造神圣的气氛,因此,宗教仪式音乐无论是赞美诗 (Hymns)、赞颂(Chants)、神咏(Oratorios)、弥撒曲(Missals)等等,都是赞颂型曲调。在近代基督教改革中,为了同信众和时代好尚相吻合,增加了不少其它内容并配以为信众所喜闻乐见的曲调,但是,由于宗教仪式结构的核心是依靠演说传道来完成的,宗教仪式的关键时刻是不使用音乐,不依靠音乐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宗教音乐内容和形式的单纯性,神剧和宗教清唱剧的音乐是极其丰富的,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宗教音乐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宗教仪式音乐。而与这种情况不同的中国道教音乐,特别是正一派道教音乐在宗教仪式——斋醮法事中的运用是贯穿性的,道教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多样而丰富。这一特点亦是由道教宗教仪式的结构和内容所决定的。道教的斋醮是以演习道教科仪的各种陈式为其主要手段,古人认为,这种演习就可以达到在《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八斋名钞中所指出的那样:“上消天灾,保镇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生死受赖,其福难胜”的目的,经过长期的演习,也就是在长期的宗教艺术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配合和渲染法事情节、并贯穿于法事始终的道教的宗教仪式音乐。从唐代以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音乐不断吸收各种其它音乐,使音乐和斋醮法事内容的结合日益紧密,形式日趋多样,以致斋醮仪式由开始到结束,包括中间情节的变化,都由音乐把它贯穿起来。道教诵唱歌曲约在元代之前,逐步形成了“步虚”、“颂”、“赞”、“偈”等几种格式,其每种格式有多种的曲调和词。以上海为例,如“步虚”,首句“太极分高厚”和“昔在延恩殿”这二首的曲调完全不同,前者是羽调式,后者是商调式。如“偈”,则有“水偈”、“香偈”、“三清偈”等等。同时,每个曲调又可有多段用途不同的词。如《风入松》曲调,有首句“袅袅烟云翔”和首句“银烛光耀红”等二种词,有的曲词甚至多达数十种用途不同的词。道教音乐的步虚、颂、赞、偈,就其单独形式来讲,是一首歌,其中短小的是上下句式或四句式(起承转合)其中大型的有复杂曲式或回旋曲式,但在道教斋醮中,并不是单独使用一种词或一首曲,而是以法事情节组合串连各种步虚、赞、颂、偈等道曲。比方说我们把每首歌用英文字母替代的话,在这一出法事中,音乐的组合是A—B—C—D,而在另一出法事中则是A(1)—E(2)—C(3)—F(4)。(字母下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同歌异词)。这种类似戏曲板腔运用的方法,我称为是道教音乐的贯穿性和情节性的特点。而当具有这种特点的音乐同念白、诵经腔、禹步、吟表等组合在一起,确实极似中国戏曲的一般模式,只不过道教音乐如果以北宋出现的谱集《玉音法事》中已有50首道教歌曲的情况来看,那么这种模式的产生,还在戏曲、戏文之前。所以,明末清初的文人观察道教斋醮的演习,象叶梦珠来说“竟同优戏”。他把道教斋醮比作戏曲,是并非偶然的。即便是近代,江南道教的斋醮也还是这样,在过去一般农民的心目中,看法事就象看一场戏或一场音乐剧一样,而实际上是一场宗教仪式的“演出”。中国道教的宗教仪式——斋醮结构上的特点,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教音乐的贯穿性和情节性的特点,必然要求道教音乐多样性而不能单纯性,而道教音乐的丰富多采的根源就在于此。例如斋醮仪式中,除了赞颂型的音乐曲调之外,为要表现的应召前来而运用急促节奏或飘拂飞翔的音乐;为要表现镇煞邪魔而运用气冲霄汉或庄严威武的音乐;为要表现众神抵达或功成庆祝而运用热烈喜庆的音乐;为要表现引上仙界而运用缥缈恬静的音乐等等,丰富多采的道教音乐在斋醮仪式中的运用十分自然。只要稍作研究就可知道,道教音乐实际状况远非有些人所误解的“死气沉沉”、“毫无规律和内容”的东西,而有着它高度的艺术内涵和强烈的民族特点。
在道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关系上,道教音乐是一种带有中国各地地方音乐特点的道教音乐。这个地方音乐特点表现之一:同一主旋律的赞、颂、步虚、偈等,各地的行腔、旋律装饰 (民间音乐称之谓“加花”)都带来本地地方音乐特色而演唱起来各不相同。例如同一首步虚曲调,苏州和上海在演唱上,苏州带有苏州地方音乐的特点,成为苏州腔。地方音乐特点表现之二:同一首词的赞、颂、步虚、偈等,各地选用本地音乐特点的旋律,词同曲不同,例如同一首《三清偈》,广东的是广东曲,台湾是台湾曲,上海是上海曲,各不相同。道教是产生在地大人多、方言和音乐各地不同、民歌和民间午蹈风格各异的中国,因此,它的斋醮科仪有统一的经典,而它的音乐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古代道教这样做,是明智的,是符合人民音乐欣赏的习惯的。道教音乐到底受到多少种地方音乐的影响呢?这个问题现在尚无精确的统计,就上海地区看,正一派道教就有无锡、苏州、杭州、宁波、本帮(即上海)的区别,由此推测,道教音乐受到民间地方音乐影响的,约在一百种以上。因此,综合观看中国的道教音乐,它本身就是百花齐放的局面,说它是汇集中国民间音乐的宝库之一,是非常正确的。道教斋醮仪式使用地方语言并以具有地方音乐特点的道教音乐贯穿始终,这和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音乐又有着较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的音乐是丰富的,数量也很多,象基督教的赞美诗这一项,据说有几千首之多,各堂口可以任意选用各种音乐曲调,所以,各国各地各堂口所选用的音乐也是各不相同,并由此也可以形成一种地方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和各堂口之间的差异仅仅是选用作曲家的不同,或者是信众欣赏口味的不同,和堂口所属当地的民间音乐无关,因而,欧美的宗教音乐并无地方音乐的特点可言。诚然,道教音乐的具有地方音乐的特点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和斋醮活动地点以及音乐在斋醮中的作用等关系甚大。道教的斋醮仪式,特别是江南和南方诸省的正一派道教的斋醮,除了少量在宫观中进行,绝大多数是在地方民众的集会和信众家中进行的,即在“庙观以外”的地方活动。同时,道教音乐配合斋醮,除了感动神灵之外,还有安抚和警戒信众的作用,《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八引“太真科”中说;“斋台之前,经台之上,皆悬金钟玉磬……非仅警戒人众,亦乃感动神灵”。在信众中活动又要使信众受到触动,如果不以他们熟悉的方言及音乐曲调,怎么能达到目的呢?道教音乐的地方音乐的特点,正是顺应斋醮活动的地方以及它对音乐作用的要求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众的欣赏习惯的条件下,不断地发展和积累,致使中国道教音乐出现了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不甚了解道教音乐这一特点的人们中,往往以欧美宗教的“统一”的宗教音乐的观点来研究道教,由此轻率地作些无益的推测和结论。例如民族音乐研究所编印的《湖南宗教音乐》的道教音乐章的第七节《各地道教音乐之间的异同》一文中,他们从搜集的实际情况中,已经看到“各地道教音乐之间,互相不同的部份也很多”,但他们面对这个“各地不同”,却是从“这可能是由于道教的仪节内容,本身就没有一套完整的严格的规定”的方向去推测。这种结论正是他们对道教音乐的中国特点缺乏研究的表现。可以想一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历来不正是和道教音乐一样的处在“各地不同”的情况之中的吗?为什么我们称它是“丰富多采”,是中国音乐的“特点”,而对道教音乐的“各地不同”却会去作“没有严格的规定”等等的推测呢?这种无形之中用欧美宗教音乐的情况和理论来套中国的宗教音乐问题,当然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看到,道教音乐带有地方音乐的特点,不但受到信众的欢迎,反过来,它又对道教的发展传播以及与农民的联系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诚然,道教音乐的特点远不止以上三点。例如:道教的斋醮仪式中往往穿插进不属于宗教音乐范畴的民间音乐、戏曲等。道教音乐应用的场面往往很难唱歌奏乐,元人所编《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三云: “施主追悼之际,惨戚装怀,讴歌词曲,尤为不便”。但在长期的实践中,道教音乐从“不便”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解决办法,使哭丧变为闹丧,在音乐的艺术创作上呈现出一些规律,等等。
应该看到,道教音乐作为一种宗教音乐,与欧美的宗教音乐有相同之处,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又有与欧美宗教音乐的不同之处。因此,研究和估价道教音乐,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欧美的宗教音乐理论,而应该从客观事实出发,以中国道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内容与特点作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总结出我们有关中国宗教音乐的理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道教音乐的中国特点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