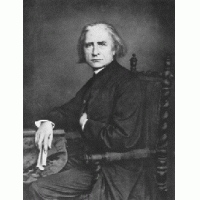布鲁诺·瓦尔特 布鲁克纳与马勒
有一种否定他们之间关系的说法,在我看来真是很特别。他们是被在理查德·瓦格纳里的巨大体验感动了,在他的艺术里看到不朽的信心,他们的作品却并未露出什么(除了布鲁克纳的器乐受了些微弱的影响)瓦格纳派的痕迹,有,至多也就是一点点,他们自己完满自足的信念一点也不受其袭扰。他们的个性里有如此强健的禀性(处在那个时代的音乐史中真叫人诧异),尽管耳界大开,心智开放,也对瓦格纳式的海妖之歌坦然表示推许,但他们就不肯屈从。当然,身为本质上的交响曲作曲家,他们平等地看待这位对他们的独立自主袭来威胁的剧作家,就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而言,好象他们在天性里就有种追求整饬结构的强烈欲望,只是基础不同而已。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位都不为戏剧舞台吸引,马勒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他通过无与伦比的演释艺术表现了再生歌剧的天赋,在那片天地里辟出一条新路,实际上开创了一个传统。他的唯一一部歌剧稿本是他早年两次失败的尝试,此外他再没有为舞台写作,除非我们把由他编写完工的威柏《三个平托斯》也拉扯进来。
他也象布鲁克纳一样在纯音乐里扎下了根,守护他从诗篇里得来的灵感,就跟他在那些歌曲里一样。然而他的作品果真就扎根在纯音乐里吗?他的第一交响曲(本来有个名字叫“巨人”)中的“卡洛风格葬礼进行曲”、第二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中的歌唱性乐章、没有标题胜似有标题的第三交响曲(修订版),这些也就是布鲁克纳所认为的原汁原味的交响音乐?无疑马勒的音乐与布鲁克纳不如预期的那么相似。他受到很奇特的意象和幻想的引诱和感召,比布鲁克纳有了更多的想法,这来自于他不那么让人明白的、隐秘的心灵深处。但是这就能说明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差异吗?不是贝多芬的“田园”里,无论“溪边景象”、“乡间节庆”和“暴风雨”都是纯粹的交响音乐,而它们自己却不大管什么纯粹不纯粹吗?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音乐创作的基本步骤吧。作曲家蓦地捉到个乐思,真真地就在那儿,在这之前那儿显然什么也没有,也许只是一抹情绪、一个影象,可是突然变成了音乐,来了。有了一个主题,一个动机,现在它在作曲家的手里塑造成型,展开它,引导它的方向,新鲜的念头蜂拥而来。无论是否在创作加工过程中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意象,都还仍旧维持了音乐本质上的“天赐”和交响结构的动力,这个决定性的要素支配了最后的成果。这种“天赐”和动力为马勒所承认,布鲁克纳也表示接受。因此,不管这个影响马勒的乐想或幻象怎样,他的根子还是扎在纯音乐里的。
退一步说,难道我们就知道布鲁克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连莫扎特,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就没有受到过一个意象或什么念头的拜访,还是他们脑子里的很多想法都是下意识里升起的海市蜃楼,没有转变成一些有意为之的方法,从而获得更为生动鲜明的色彩和更具个体风格的特性?歌德的小说《亲和力》中,在爱德华和夏绿蒂夫妇办的家庭聚会期间,奥黛莉完全占据了爱德华的目光,而夏绿蒂的眼睛也牢牢抓住了上尉。尽管出生在这样的结合下的儿子令他们心里神游的梦幻大为烦恼,但他也毕竟还是爱德华和夏绿蒂的后代,是从他和她的自然结合里生长出来的。无论在创作的过程中音乐以外的想法有多大影响,起始总是很神秘,而纯音乐就是结局。但若这个作曲家的意图就在于要真正地叙述什么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使得音乐开始描述一个想法或者意象,那么,他自己就得先把纯音乐的口子堵上。
在马勒眼里好象布鲁克纳的音乐从来就不意味着一种要表达什么的方法,它就是它,更无其他,他自己则从未忽视过这种天生的对于表述的兴趣。其实这是他俩在其中灌注生命的一个要素,由他们的天性推动到交响音乐的形式。马勒施展魔法造出的昏天黑地里充满了激烈变幻着的梦境;布鲁克纳则还是为崇高的幻象所主宰。由于布鲁克纳(就我所知)直到1806年他故世时也不大熟悉马勒的作品,反之后者则十分精通布鲁克纳的艺术,这就要使我们考虑布鲁克纳的影响力是不是就没有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起到什么作用,没有在马勒心中引起血肉相亲的感想。应该说这里面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毕竟,也没有什么影响是能强加于他的,况且马勒独特的音乐语言也并没有什么依托于布鲁克纳的迹象,无论让人觉得相似还是引起回想。但我们还是在他的主要作品之一——第二交响曲里看到这种深厚的、本质上的血缘关系的暗示,并且直到他最后的作品里还能碰到偶尔一见的“布鲁克纳”特性。不过他对布鲁克纳的依赖也就是一点点,就象勃拉姆斯对舒曼一样,后者的很多“特性”时而会在勃拉姆斯的作品里神出鬼没地闪现。浮士德有关拜伦的论断可能对这两位也是适用的: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位都赞成“我歌我自歌”,也就是说——独创性。
什么使他们分开?
布鲁克纳的九部交响曲都是纯粹的器乐作品。马勒则不同,在第二、第三、第四、第八交响曲里借助了歌词和人声。交响曲以外布鲁克纳作了三部弥撒曲,感恩赞,“诗篇”第150篇赞美诗,一些圣咏作品和(就我所知)两部男声合唱。马勒迥异于此的标志是他的非交响乐作品。他写了“悲哀的歌”,奠定了他自己的叙事诗;四个章节的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歌词也是他自己作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则得自“少年的魔号”中的诗篇;再往后一个时期,为吕克特的诗篇作乐队伴奏的歌曲,其中有“亡儿之歌”;还有他最后的、流露了最多个性特征的“大地之歌”,歌词采自中国诗人李太白的作品。因此,我们看到布鲁克纳就和他的那些交响曲在一起,几乎完全浓缩在神圣庄严的乐章之间,而马勒则从五花八门的诗篇里获得了灵感。在他的交响曲里,“原光”是来自“少年的魔号”,而克洛普斯托克的“复活吧”给予了他的第二交响曲一个庄严而欢乐的结局,在第三交响曲里,尼采的“午夜梦寻”在第四乐章发出预兆,再由“少年的魔号”中的诗篇在第五乐章作出回答。通过这样的搜集,马勒选择了一些具有童心般的信念的诗篇,为他自己祈望的天庭生活作了象征性的描述。第八交响曲起始于“降临吧,创世主的圣灵”而终结于浮士德对信仰的皈依。
因此马勒的声乐作品同时也是一条了解他的心理世界的线索,它们诉说了他通过发现和不断的追寻,经由越来越深的直觉和更加崇高的向往去贴近上苍的努力。然而就在被这一点占了主导位置,仿若他生命中的“固定音型”的音乐里,也始终回响着其他的声音,借由相伴的诗行细诉:爱与死,无力自主的生命与光怪陆离的世界,幸福与悲哀,玩笑与绝望,勇猛的挑斗和最终的顺从,在所有这些雄辩的音乐里透出个体生命强有力的表述。要是我能对这两位大师的不同之处只用最少的几个字说清的话,那就是(且带点夸大其辞):布鲁克纳的精神在安息,而马勒则不得安宁。布鲁克纳最为热情洋溢的乐章里都有一个稳妥的根基;马勒则连最隐秘的地方也不得安宁。布鲁克纳的表述范围是无边无际的,尽管他只说出了很少几个要旨;马勒则是大肆挥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抱住了所有的阳光和黑暗,一种滑稽的插科打诨,甚至不避怪异和老一套,还要加上对着爆发的骚乱,象个大感兴趣的孩子那样数不清的表情变幻。他诚心诚意的民间主题由于那些冷嘲热讽的腔调而成了“马勒制造”,闪电和幽灵一道画出他音乐风景里的漆黑夜色。他也有高贵的平和与肃穆,曲中高妙的变形就是这样的成果,而那对于布鲁克纳却是老天赏下、与生俱来的;布鲁克纳的音乐信息得自一位圣徒,马勒则为一个激情澎湃的先知发言;他永远在开始新一轮的战斗,又总在结局里变得乖乖顺顺,而布鲁克纳的音乐世界则渊停岳峙,宣吁人心慰安。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其本身并没有用到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布鲁克纳的音乐还是如有定数一般,在一片相对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疆域里撒下无穷无尽的财富,他最常说的两个词“肃穆”和“挚诚”也指示着这种方向。似乎这样就足够了,他无须再借助于千奇百怪的诙谐,让我们象沉浸在哥特式大教堂那滑稽的外部装饰里一样。甚至连他的管弦乐法也很少有什么变动。第七交响曲里他加了支瓦格纳大号,第八里用到竖琴,但就是这样他的乐器安排还是根本没什么改变。从第五交响曲开始的和声与复调的性格以后也不再变化,尽管(也确实如此)它是十分丰足而有灵性,也无须再变了。
上一篇:莫扎特生平简介
下一篇:温德青谈现代气质与民族风韵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