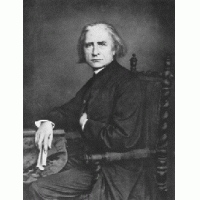威廉。福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的音乐观
(一)我绝不刻意去迎合听众的胃口
陈列在我面前的乐谱是最重要的,我需全神灌注地投入其中,并设法接近它,我若能把乐曲内涵忠实地表达出来,那么听众就能同意我的诠释。但我绝不刻意地去迎合听众的胃口,主要的原因是每一位聆赏者之理念均不尽相同,他们也可能禀赋不同层次的音乐接纳力,以及不同层次之接纳意愿,不是吗?听众们是绝不相同的,譬如说英国和美国的爱乐者对交响曲的接纳态度,与其它地区的爱乐者比较,则有显著地不同,英美爱乐者认为交响曲就是把数段主题旋律以交响曲的形式演绎出来。而一首交响曲在本质上俱备着其原始理念,此理念需在整首乐曲完完整整呈现出来以后,始能彻底地被了解。一首交响曲常由二个三个或四个主题旋律交替出现所组成。成功的谱曲经营应使各主题旋律能相互衬托。而终各自发展成类似莎士比亚戏剧中以赋予生命力且各具个性的角色。在乐曲中再现的乐段,应与第一次呈现出来的方式迥异。因为在乐曲进行过程中,各声部错综交替,所以对一首乐曲的印象也是建立在各自乐旨间的复杂关系上,乐曲的效果绝不可能得自单一主题旋律之表现,而是衍生自两个不同主题之对比。你当不至于认为有感情的音乐始自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吧?

(二)弦乐部的弓法是否得强制,常是作品性质而定
乐旨或乐段的特征以及其发展方式决定了乐曲将择何途径作最透澈的表达。有些乐段,比如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并不需刻意去要求小提琴的弓法要整齐划一,当然会有人认为他的某些作品里,不整齐划一的弓法,将影响乐曲本身的品质,故有时对小提琴手们所使用的琴长度有刻意要求的必要。像我最近所指挥演出的亨德尔协奏曲的尾段,有持续之弦乐器振?这时以不一致的弓向,可使乐曲不显现出中断的感觉。但是一般来说,为了重音
位置之强,不管是小提琴或大提琴,均习惯于乐谱上明确地注明了上弓、下弓的换弓向位置。
(三)没有绝对正确的诠释
在两种不同之演奏版本中,绝难去举证那一版本的诠释及速度的处理有错,或那一版本比较更符合作曲者的精神?不论在古典作品或现代作品中,那些构成乐曲完整性或对比性的音乐素材,均是决定乐曲速度应缓应急的重要因素。作曲家常始抒情性的旋律倾向于慢节奏来表现,其他的过门则倾向快节奏,至于如何在此两极端间去谋取调合,并决定出一个适当的节奏,这就是诠释者在判定乐曲速度时所要做的努力。速度本身与乐曲诠释的完整性之间存在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其精神层面的存在价值,乐曲速度的取决,通常根据乐曲本身所具备之特性而定。
(四)布拉姆斯、雷格与马勒对演奏者的指示
布拉姆斯对谱曲的经营,有其一套逻辑思维之脉络,与瓦格纳比起来,他绝少在乐谱中附加演奏指示,但这一点却使他显得更成功。Reger在某些层面上来说,应可视同布拉姆斯的学生和继承者,但Reger的谱曲理念。却与布拉姆斯相左。Reger在乐谱中使用超量的表情记号,在Reger的一页乐谱中所注明的演奏指示,将超出布拉姆斯整首交响曲的总和。马勒的作品则又不同。他本人对管弦乐团有实际接触的经验,马勒在乐谱中注记演奏指示,要求演奏者要照章办理,但事实上如果完全照指示演奏,则其结果将未见完善。譬如在齐奏乐段,马勒在乐谱中注明各种乐器均以ff音量奏出,其结果是聆赏者只听到长号及小号的尖响,其于则全部被铜管乐声淹没无踪。我想马勒听到了如是的演奏,一定会说“那是不对的”。若依我的,会把小号的声量降至f或mf,这时单簧管的乐音则可显露出来,这才是马勒的原始意图。
(五)布鲁克纳交响曲的修订版与作曲家原旨不合
这些我们讨论的细节,另引导我们步入布鲁克纳原版本交响曲所存在的问题之核心。原版本与后代出现的修订本之间的区别,撇开速度记号的修改不谈,修订版有的地方之修改方式,则显得过份离谱且外行。布鲁克纳的两位学生沙尔克及洛威,就是修订版之主事者。他们将原作依实际演奏的需要,而把乐曲长度予截剪,但也因这些截剪,常使得原作旨意丧尽。但无可否认的,有些修改却是颇具效果,而且也显得是绝对的需要。如果依照某些
音乐学者所冀望的方式演奏,其结果将不尽人意。
(六)布拉姆斯对表情记号的运用持保守态度
除非是绝对的必要,否则布拉姆斯绝少在乐谱中使用表情记号,不过一旦用上了,必呈现其存在的适当及必要性。他在乐谱中如注明了ff或p则我们可藉演奏效果来印证这些强度记号确实使用的非常正确。而事实上,也绝少使用像ff这种夸张的强度记号。大致说来,别的作曲家可能用上fff或ff记号的场合,布拉姆斯总仅含蓄地记载著f。瓦纳的配器法很实际,尤其是他中期的作品,一特征明显,曲表现出来的声响美极了。假如依乐谱的指示,忠实地演奏《女神》与《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两出乐剧,你将发现,整个管弦乐团各声部的声响是多么的和谐及匀称。
(七)表情记号在实际演奏中,多少受到限制
在表情记号的使用方面,瓦格纳始终表现了如许的逻辑及机智。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位善于表达情感的戏剧人物,使得他在音乐作品情感表达方式运用上,显出无上的权威。他的乐谱中,不论是强音、弱音、渐强以及其它的表情记号,一定非常明确的指出位置,绝不可能被误解。他惯常于写绵延不断的旋律,有时一段旋律即长达一页乐谱。但他绝不在乐谱上为提琴手标明弓法,而把换弓向的判断交给演奏者来注记,这种作法是正确的,因弓法
本来就是提琴手的演奏实务。但不幸的是,指挥家在面对华格纳的乐谱时,却常需费神去关注弓法等等细节。假如指挥者不对提琴手之换弓向位置予明确地注记,则提琴手多会依自己的习惯换弓但其结果常是错误且乐音显得突兀。而以上所讨论的将引导我们谈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大家晓得古典乐派时期莫扎特及贝多芬的作品中有圆滑奏的乐段,而在他们之前,使用连结线最长的,也仅跨及一小节时值。但在瓦格纳的作品就不一样了,他的连
结线却从头到尾涵盖一整段的旋律,试图表达出作品中完整而成熟的思想,而不理会此旋律应如何予以分成段落。但用连结线要求乐手以圆滑奏贯通整个旋律线之意图,却有其先天性的限制。譬如说琴弓的长度是有限,所以一定需要改变弓向,歌手及管乐演奏手需要呼吸换气,我认为巴哈作品的感情是蕴藏在其旋律线中,当旋律线被正确地演奏出时,这蕴藏其中的感情就表现出来了。
(八)优美的歌声并非演出成功的保证
当要评断一位演唱家的歌艺时,很有趣地我们将发现到一位配有良好伴奏的演唱家,就能现出最好的演唱效果,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歌手均然。至于其道理何在,迄今学理上尚无明确定论,而且也绝不可能以学理来作衡量尺度。从经验我得知,有某些歌艺平凡的女演唱家,在良好伴奏之搭配下,却能创造出比杰出的演唱家更良好的演唱效果。歌手在剧院演出时,需能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出来。有些人却没能达到要求的水准,他虽有足够的才华
,但可能始终发挥不出来。他们或许能将艺术歌曲或巴哈的声乐曲唱得很杰出,但却无法在剧院里精采地演出歌剧。譬如说在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光会唱咏叹调是不够的,演出的歌手尚须把他个人丰富的人生经验溶入舞台,才能演出“魔笛”中角色的精髓。
(九)《魔笛》代表反璞归真的境界
我很难把“魔笛”这出歌剧作适当地归类,依文学的观点来说。他独树一帜且别具一格。如同莫扎特另一出歌剧《后宫诱逃》一般,它起初记划写成一出德国式的轻歌剧(singspiel),却逐渐演变为完全两样的型态。在某一方面,他可称之为莫札特藉以传述他对共济会纲领之服膺的共济会式歌剧。而在其它方面,他又代表了日后轻歌剧(operetta)的前驱(就一种非常高的水准)。莫札特企图在不放弃他最崇高理想的原则下,尽可能使每个人都能了解它,这也是它所以会显得独一无二的原因。依我看来,只将《魔笛》当作一个童话,一出壮观的歌剧,一出严肃的神秘剧,或任何人所想的任何作品型态,也就是说将它限制在某人能力所了解的领域中,那是“伪智”的象征。我们必须了解,《魔笛》一剧包含了万物,这是现代人很难明了的关键。我们总想寻出并证明每件事物背后的基本概念,当现代人能够说服自己相信它只是一个童话,或任何它认为它是的东西时,就显得极为快乐--他要的是概念。而在这里,我们寻找的是一种远较概念伟大的东西--本质,就是它方能令这出歌剧独特。《魔笛》并不是一出像《费加洛婚礼》般的罗可可风格歌剧,也不是像“唐乔凡尼”般的形式扩大了的巴洛克歌剧,或是莎士比亚风格的作品,它是颇为不寻常的。
(十)瓦格纳在乐剧创作方面,确实匠心独具
瓦格纳掘起自一个歌剧写作不甚要求歌曲字眼被清晰听到的时代,他的创作观认为,一出真正的乐剧应强调演唱时,歌词咬音要能够被聆赏者清晰地听到。在拜鲁依特歌剧院中的演出效果却是优劣参半。管弦乐团的声响在拜鲁特歌剧院中则显得相当沉闷,就好像闷在一个袋子里发出的声响一样,假如要勉强讲出一个意象来形容这种
感觉,则人声部份有若被隔著一只空桶来发出声音一样,且漂浮在管弦乐团的乐音之上,正如浮油在水上一般地层次分明。假如演唱的好,则歌辞可很清楚逐字地听出来,但华格纳企图表现的绚烂及富美感的管弦乐乐音,就无法有效地表现出来。但乐剧《帕西法尔》的情形则不一样,瓦格纳在汲取拜鲁特演出《指环》的经验后,刻意地经营了《帕西法尔》的配器及修饰过的管弦乐法,故此剧在拜鲁依特演出的管弦效果,依他预期的全面改观
。我犹记得,1912年在拜鲁特由李希特(Hans Richter)指挥演出歌剧《名歌手》,那是我所听过之所有瓦格纳演奏会中最好的一场歌手在不自觉置身于歌剧院中的状态下,演出歌剧方能使演出成功,这时演出正如日常会话,言词抑扬像是简易的话剧一样自然。至此,我已深刻地了解到瓦格纳确实胸有丘壑,每出乐剧均有其刻意经营之预期效果。当我指挥瓦格纳的乐剧时,我总喜欢让管弦乐团在较宽敞的会场演奏,因为如此安排,管弦乐团的声响比较绚烂,而且与人声之间也显得调和,当然最重要的尚需搭配一位善于“伴奏”的指挥家。
(十一)必须先了解威尔第与华格纳的共同点,方能探索其差异
威尔第在完成歌剧《阿依达》后十三年,开始再谱写下一出歌剧《奥泰罗》,这种“沉默”对一位正透过一连串的杰作,而赢得世界性赞誉之炙手可热作曲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事。不管威尔第是什么理由中断了创作,但此中断也似乎意味着他正被塑造成与大部份德国作曲家不相同的形象,而瓦格纳可能就是他急于挣脱的影子。威尔第让自己稳固立足于写实主义中,虽然这亦即是德国人一向在真实世界中所追求的精髓,而歌剧《奥泰罗》可视为同是威尔第与莎士比亚两种艺术的综合追求的最终极目标,且两人均是伟大的音乐家,也均懂得如何去运用音乐素材去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境界。瓦格纳汲汲于让聆赏者能步入他诗般的意境,威尔第则重视戏剧效果,而两者则均代表人类借由歌与演来表达内在情感的最高极限。莫扎特常被认为代表著德国与意大利文明之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