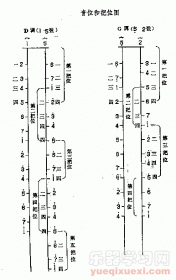历史进入了20世纪20、30年代,在我们民族音乐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位天才大师刘天华的出现,把二胡艺术一下子提升到空前的地位与品格,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民族乐器中的佼佼者。刘大师驾驭以来,他的十首二胡名曲,自诞生以来的八、九十年中,是每一个学习二胡的人(不管是院校科班或者自学)必修之课。但真正能深刻理解与领悟刘氏作品的内涵与精髓,并能较完美地加以演绎表达,尤其是对刘氏作品诞生的历史背景、创作意向、艺术手法等作深入了解与把握,然后再去演奏,这样的人往往为数不多。
刘天华作品诞生近一个世纪以来,能够真正对刘氏十首二胡名曲,不仅从作曲手法,而且能结合人物时代背景以及与西洋音乐的比较,并结合中国古典诗词,甚至涉及到音韵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学科来进行全面、系统、深度的研究,撰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文章,还是从《音海琴韵——潘方圣二胡论文集》出版才实现的。
张韶在给潘方圣先生写这本书的《序文》里曾说过:“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博览群书并有深厚古典文学基础和音乐修养的二胡评论家。”此话如何说呢?举例说明:
在分析《病中吟》一曲中,潘先生在对这首曲的曲名来历探讨与分析,就有这么一段话:“‘吟’是古代的一种诗歌或乐曲的体裁。例如,在魏晋时期就有‘歌、曲、乐、引、行、吟、操、弄、拍、讴、怨’等体裁形式。如上古的《南风歌》、《采薇歌》;相和曲《箜篌引》、《罗敷行》;平调曲《从军行》、《燕歌行》;楚调曲《泰山吟》、《梁甫吟》;清商曲《江南弄》;杂曲歌辞《游子吟》,等等,以后这些体裁名称就一直流传了下来。像唐代有名的孟郊《游子吟》、白居易《秦中吟》等。现在这种体裁在古琴曲中遗留的最多,如《别鹤操》、《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良宵引》、《春晓吟》、《昭君怨》等。明代王骥德《曲律》中在讲到各地的方言腔调时,也用了秦声、赵曲、燕歌、吴歈、越唱、楚调、蜀音、蔡讴等称谓。实际上这些不仅是强调与突出了各地腔调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了汉语同音词汇的丰富。因此,这些体裁从现在来看,已体现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用之能给作品披上一层颇具古风的意味。由于刘天华有着十分深厚的古典文学与音乐基础,因此,他十分偏爱运用这些乐曲体裁名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多么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与功力。又如:在分析《烛影摇红》一曲中,对曲名的探讨与分析,指出:“此曲的曲名是借宋词同名词牌而来的。‘烛影摇红’原是北宋词人王詵《忆故人》首句的前四字:‘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沈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当时著名词人周邦彦用它作为题名另作新词,后来就成为一个词牌了。刘天华用词牌来作为曲名,也仅此一首。”没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功力的人,能这样旁征博引、左右蓬源吗?在分析乐曲的艺术手法时,指出第一句音,“旋律由最高音从上而下具有一泻千里之势。从文学上讲,使人想到了词中领字的气势与作用。领字通常用去声字,因为去声字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声调趋势。因此,‘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当用去者非去则激不起’(《词律·发凡》)。例如:‘看万山红遍’(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看’字。······因此,此曲的引子是从最高音开始,一路下滑至低音,开始的高音就相当于词中的领字了。······器乐曲中更是多见了,尤其是小提琴中运用和弦强音击奏,然后跳高八度一路下滑的奏法是很普遍的。······也使人想到很多钢琴曲,如肖邦的《波兰舞曲》与《诙谐曲》等节奏鲜明的三拍子节奏;肖邦的《夜曲》中令人陶醉的散板等在此曲中似乎均可找到它们的影子。”没有通晓现被称为‘国学’的古典文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学科知识和熟悉西洋音乐的人能写出这些文字吗?对刘天华的研究,早已有人在做,文章也不少见诸报刊,但能把刘氏的十首曲全部地进行系统、全面、深度的研究并撰写有独到见解的十篇论文,这在国内乃至全球,潘先生实属第一个人。另外,本书对我国二胡史上一些大师及其作品,如阿炳、蒋风之、刘文金、刘明源、彭修文等,对他们的作品与成就,均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研究,这在国内也是第一个人。说明作者平时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深厚积淀的结果。同时,本书对我国二胡史上不同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经典名曲,均作深入浅出的分析与研究,这在国内也是第一个人。总之:本书是二胡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本二胡论文集。无疑,此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二胡事业,尤其是二胡理论研究事业,必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全国各地大中院校学二胡的莘莘学子不少,但只是一味追求技巧的炫耀,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与艺术素养,此书正好是一本较好的教材来弥补此缺陷。包括现在一些年轻的二胡教师,我们建议他(她)们也好好地研读、学习此书中的一些文章,对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与文化素养,从而更好地教好二胡,不是没有好处的。最近传来一个十分可喜的信息:潘先生的《论刘天华十首二胡名曲》被美国一家音乐刊物全文发表。这恐怕是研究刘天华有份量的学术文章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境外音乐刊物用英文第一次公开发表,从而使我们的二胡学术和对刘天华的研究走向世界!令人寻味与不可思议的是,上述这几个“第一个”,这一切竟是一个二胡“业余爱好者”来完成的!(潘先生是党政机关的一名公务员,数十年如一日爱好二胡而为之。)潘先生在二胡界没有什么“职称”、“头衔”之类可以炫耀的东西。他平时只是埋头做学问,很少抛头露面,因此,在二胡界也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有些人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把他贬之为“业余爱好者”而不屑一顾。这,究竟是潘先生的悲哀,还是那些贬低他的人的悲哀,抑或是这二者兼而有之的悲哀?!
我们二个人,一个84岁,一个91岁,一生都是贡献给二胡事业。我们的一生见证了二胡事业在刘天华大师出现、驾驭以来蓬勃发展的历史。但现在令人担忧的是,二胡界重演奏、轻理论;重技巧、轻素养;重“眼感”、轻“听感”。尤其是对大师刘天华留给我们后人这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的力度、深度和广度,缺乏应有的认识、研究与传承。这不得不令人叹息与三思!我们希望:《音海琴韵》的诞生,给中国二胡界乃至整个民乐界以启迪,少些浮夸之风,多做像潘方圣先生那样脚踏实地的工作,使我们的二胡理论研究事业更好地传承发展下去,后继有人!我们拭目以待.
上一篇:二胡千斤宽窄和琴码高度再探索
下一篇:二胡的物质结构与音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