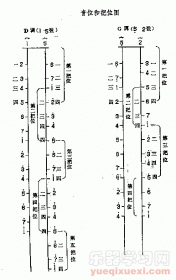说来话长。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正春暖花开时节,我出差由武汉乘江轮至上海。入夜,我在甲板上散步,听到船尾处传来悠扬的二胡琴声,是谁打开了收音机?我循声寻去,只见右舷的栏杆旁,一位秀发披肩的姑娘,沐浴着月影星光,手执一把二胡,正拉得如痴如醉。她拉的是我熟悉的《二泉映月》曲调,只是比我平日听到的更为悲怆一些。默默聆听,姑娘的琴声仿佛是失群的孤雁在哀鸣、北风在漫天黄叶中呼啸、哭丧妇在野坟断断续续的抽泣……撕裂人心的琴声给人以压抑,让我忘却了身边的春江花月夜。月光下,依稀可见姑娘白皙的脸上挂着两行清泪。我不理解她年纪轻轻,何以有如此的沉痛,这是她那窈窕瘦弱之身所能承受的吗?呜咽的琴声让我想起了动乱岁月的苦难往事……听着听着,渐渐地,我又感觉到琴声中潜藏着一股昂扬刚健的清流在激荡飞溅,与先前有些异样了。
我的心随着琴声急剧跳动,仿佛看见瞎子阿炳咬紧牙关,在风雪茫茫之夜,摸索着向前。那根细竹杆敲击着沿街的冰凌,铿锵有力的声响震撼着不平的世道,呼唤着沉睡在雪原下的春天……渐渐地,姑娘的琴拉得有些跑调了,随着她的手臂有力的摆动,只觉得琴声越来越激昂雄壮了;像鼓点、不,像号子,是黄河纤夫的号子吧?猛然又听到我熟悉的“命运”的敲门声,断断续续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竟可以用中国的二胡奏出,多么奇特,多么新鲜!正当我听得兴奋之时,“叭”只听一声脆响,弦断音绝。姑娘长叹一声,静坐了一会,便起身回舱了。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半夜索性披衣起床,又到甲板上散步。阿炳和贝多芬的心音弥漫在大江之上的广漠星空,陪伴着我,直至深更……
从那以后,我搜罗了不少《二泉映月》和《命运》的盒带和音碟,并习惯了将它们联在一起聆听。特别是当我遭遇逆境,中了小人的伏击和暗算,心情郁闷之时,这两首乐曲总是能让我从颓丧中昂起头来。听这两首乐曲,仿佛是在听瞎子阿炳和聋子贝多芬的对话:他俩一个在漆黑的冬夜伸手摸索绚烂的朝霞;另一个则在死一般的寂静里寻觅春雷的轰响……面对苦难决不屈服——这就是跳荡在这两首乐曲中共同的心音。瞎子阿炳和聋子贝多芬是亘古未遇的知音。
我深知,这二首乐曲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她不是那种甜美轻巧的艳花丽草,而是动人心魄的人间大美。创造这种大美,常常需要付出常人以难想象的代价,经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如同传说中的灵芝仙草总是隐身在人迹罕至、虎蟒出没的险境,采撷她需要以生命作代价。阿炳的眼瞎和贝多芬的耳聋,都发生在他们的二十五岁左右,恶魔的黑手过早地掐断了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们的主要作品都诞生在残酷的黑暗之后。这个不幸的事实,似乎在揭示一个不幸的箴言:艺术的辉煌往往孕育在悲剧性的人生中,无限风光在险峰,美的创造充满艰辛。
如此说来,做一个有成就的真正的艺术家似乎必然会遭遇苦难,这对于那些纯真善良的艺术家来说,真是残忍和不公平!可事实一再证明就是如此。这难逃的宿命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聆听《二泉映月》和《命运》时,我常思考着这一问题。那动人的旋律中有一个多么优美的灵魂、多么高傲的灵魂!艺术家的傲气与傲骨使他们难与俗共,这,也许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俗”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它循环往复又无所不在,因而极其强大。“俗”的巨手操纵着人的富贵腾达享乐之路。不与俗共就意味着对这条路的关闭和拒绝。阿炳与贝多芬不愿向权贵低头,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只能被挤兑到权力圈和经济圈的边缘,挣扎在生与死的悬崖……在阿炳卖艺为生的年代,豪门权贵开堂会成风,阿炳拒绝前往,他说:“我就是饿死也不能为那些衣冠禽兽演奏。”极为相似的是,贝多芬有一次愤然从皇亲国戚的客厅退场,结果遭到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囚禁。夜里,他砸门逃脱,亲王派管家急追并奉上密函:“您是接受我邀请前来赫热德斯基休养的客人。而您竟然不顾我的情面走开了,我不得不感到难堪和遗憾。在这里我恭候先生回来。我的请求不是软弱的表现,我的这封信也可以当作是亲王的一种命令,我以为我有权利命令您回到奥拉瓦村来。虽然您公认为是位音乐家,但您毕竟是个琴手……”贝多芬愤然扔掉这封信函,并致口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偶然成为亲王的人,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可遗憾的是,人世间趋炎附势者永远众多,这就使得权贵的报复更加凶恶无情,必置那些善良无助的艺术家于死地而后快。阿炳和贝多芬就常常遭遇到生存难题。他们用血泪浇灌的艺术之花卖座不卖钱。1818年,贝多芬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困窘的神气。”为了靴子洞穿之故,贝多芬竟不能出门。而阿炳就实实在在是靠卖艺行乞,他在街边站着拉琴,有时一天边走边拉几十里。悲惨的命运如影相随,驱之不去。这似乎应验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性格即命运。我想,即使阿炳不瞎、贝多芬不聋也难以挣脱困境。
我这样推断是因为在人类美的创造史上,还有许多不聋不瞎的艺术家都无法摆脱与苦难结伴的命运;屈原愤而投江,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浪迹天下,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莫扎特一生饥寒交迫,35岁早夭,巴尔扎克一生为债务所迫,凡高一生只卖出一张画,饮弹自尽……
苦难是优秀艺术家成长的学校。人性的真与善在顺境中常常沉睡着,被庸常所遮蔽,只有身陷逆境,抛下底层,经受磨砺,才易激活,从而靠近了难觅的美。这就是人类艺术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美走过的道路。当然,苦难不能一概而论,相对于物质的苦难,心灵的苦难更贴近美的创造。因为并不是任何苦难对任何人都会给予补偿,也不是从任何祸中都可以得福。幸运之神与命运之神的奇遇格外青睐心灵的苦难者,格外恩赐心灵在地火中熬煎锻炼后的升华。尽管一些远离苦难的凡夫俗子,通过艰苦努力,也许能创造一些寻常的美,但永远与那惊心动魄的美无缘。至于那些艺术投机分子,以种种手段,钓名沽誉,左右逢源,以至荣华富贵于一时,但最终只能制造一些美的代用品和覆盖美的垃圾。
然而,谁愿生来受苦!?追求快乐、享受人生是人的天性。世俗生活的快乐与艺术创造的艰辛,永远是艺术家抉择的难题。实际上,阿炳与贝多芬对快乐人生的渴求超越了常人。《二泉映月》和《命运》中,支撑那些不屈抗争音符的,不正是对美好未来的不可遏制的渴求吗!阿炳用琴声抚摸皎洁的月光,贝多芬用琴声呼唤化冰消雪的春雷。他们被抛入苦难的深渊,却用个人的不幸带给了人们有幸,以个人的痛苦换来了众人的欢乐。从《二泉映月》和《命运》中,人们汲取了多少战胜苦难、走向欢乐的力量。
从这点看,《二泉映月》和《命运》有共同之处,但差异也是明显的。一舒缓,一急促;一感伤,一强悍;一内敛,一外露;一柔一刚,从中透露出东、西方人对厄运与苦难的不同态度:那就是震撼一时的牺牲与坚韧不拔的忍耐。大难临头,《二泉映月》以忍耐应对,显示的是冷静顽强的防守;《命运》则以搏斗抗争,透露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隐藏其后的大背景是行将落伍的农业文明的叹息与工业文明的怒吼。东方的苦难与西方的苦难毕竟不是同一种苦难……
当然,当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知道《命运》的人很多,知道《二泉映月》的人毕竟还少。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伍遮蔽了她应有的光辉。然而,是珍珠就一定会在世界民族之林闪光。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一个春天里,被誉为世界四大指挥家的小泽征尔在中国偶然地听到中国人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他听着听着,竟泪流满面地跪下了。这位饱受西洋音乐熏陶的第一流的日本音乐家深情地说:“这种音乐只应该跪下来听,坐着听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从此,一位中国乞丐的音乐作品让世界震惊,被誉为世界十大名曲了。真正的人间大美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的,在《二泉映月》面前,被誉为东方人的骄傲的小泽征尔震惊了,我想,被誉为西方人的骄傲的贝多芬如果活着,同样也会震惊。人类在苦难中跋涉的心音是相通的,他们的对话不论是在东方和西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绵绵不绝……
写到这里,正月上中天,我情不自禁打开了音响,《二泉映月》又一次响起,接下来我又要放《命运》了。阿炳与贝多芬的心音又在青空回荡。二十多年来,从青年到中年,我就一直习惯这样聆听。这要感谢那位在船上拉二胡的姑娘了。此时,她在哪里?过得还好吗?如果她读到我这篇文章还会记起多年前船上的那个春江花月夜吗?
上一篇:苏式二胡制作考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