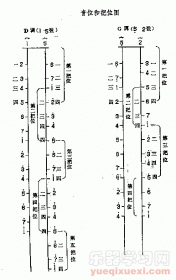当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匆匆奔赴在民族救亡大道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无动于衷,他是瞎子阿炳。他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不过是一流落街头的民间艺人,既不能上战场又不能在乐谱上作一些类似于《黄河大合唱》式的“宏大叙事”,但他有胡琴,有琵琶,有中年时因双目失明而陡然长出的一对更加敏锐的耳朵,还有一颗富于东方世界特有的宽广敦厚的悲悯之心,所以他把古老乡村民间乡里的听觉化作了晚近中国历史上最美丽凄凉和一唱三叹的音乐旋律,一首《二泉映月》,映出的是阿炳已经干涸但丰盈异常的一双关怀世道人心的眼睛,所以他是“宏大叙事”之外永远存在的一个常数,一个能让不入流的艺人和穷苦百姓听见便感怀不已的温暖的名字。?
阿炳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存在是奇迹。双目失明的阿炳总让我联想到双耳失聪的贝多芬。是不是经历了生命中最大限度的悬殊——如生与死、富与穷、无限的光明与无边的黑暗、一览无余的清澈和与世隔绝的混沌等等——的火与冰境界的人,才更加贴近艺术和生命的本体要求?“聪明”者,耳聪目明也,这不但是健全生理的最低标准,也是艺术感悟的底线,但阿炳和贝多芬们居然便可以超越肉体的毁灭性的万千阻拦,到达寻常民间艺人和寻常古典作曲家望尘莫及的高度。艺术的极境不一定非要以肌体功能的部分丧失为代价,但一定与心灵内视和俯听的质量息息相关,与天才的顿悟和冥想息息相关。?
我相信一个人内心如果常常掠过《二泉映月》或《梁祝》的旋律,那么即使面对悲苦的世界,他也构建着诗性的自我表达的空间;如果说常常掠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或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那么他肯定对痛苦置换的欢乐有极大的释放感;如果常常掠过的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或比才的《卡门序曲》,那么他一定意气风发,情绪高昂,有仰天大笑出门而去的豪情壮志了……音乐与人的对应关系如此清晰地洞悉了心灵的奥秘,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我现在怀想着《二泉映月》,我一直想着未有此曲之前,瞎子阿炳他那对异于常人的耳朵是如何陡然长出来的。?
在日军侵华时颁给各地市民的“良民证”中,我看到阿炳的惟一一张照片,他的盲镜滑稽地斜挎在鼻梁上,似两个黑洞,他那时一定被妻子董翠娣用一根细竹竿或一把折扇牵着,神色苍凉而傲慢地走在无锡的大街上,身上背满了各种乐器。他听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而听觉在一分一秒地清晰、变重、变厚,他隐忍的外表下掩藏着一种寂静和忧伤的聆听,他能听见黑暗中一部分嘈杂的欲念在慢慢离身体而去,代之以手指间滑出的一段和弦。哦,这个出身卑微的私生子,这个诵读过《道德经》且深谙以精神致魂魄的道士,这个无锡城里技艺最出色的艺人,他对生命的终极见解全凝结在那一对陡然长出的耳朵上,凝结在耳朵幻听出的《二泉映月》上啊,那是阿炳的全部,是他卓然独立于世俗民乐之外的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