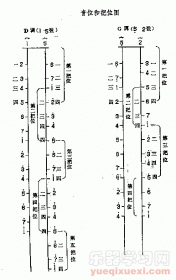|
|
|
1931年农历5月28日,享誉“胡琴圣手”的中国音乐家、胡琴演奏大师;才情横溢的作曲家、桃李满天下的民族乐器教育家刘明源先生诞生于中国天津市虹桥区。其父从医,酷爱民间音乐和戏剧,拉得一手好胡琴。刘氏天资聪颖,五岁随父习板胡、京胡七岁已在天津大戏院登台献艺。11岁开始参加天津“百灵乐团”、“闽粤会馆’等国乐社团的演奏,14岁加入就读的天津育才中学国乐团,常参加学校、国教馆及民间组织的演出活动。1952年曾涉足专业评剧(流传北方地区的剧种)的创腔、配器及演奏。同年底,受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为电影《龙须沟》录音配乐,效果理想。为此,北影将刘氏等七人留下,由此成为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乐团中国电影乐团前身)所属之中国第一支人组成的专业民族乐队之奠基人及其中坚。此机遇,可以说是刘氏一生的转折:为其开辟铺垫了一条广阔璀璨的艺术道路,并决定了他日后逐渐成就其丰硕光辉的事业。刘氏在电影乐团三十年,历任乐队首席、副队长、队长等职,曾为.上千部各类电影录音配乐。在此期间,刘氏展示了他多方面的天赋才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主要成就:
l、乐器改革的成果。五十年代始,刘氏已开始致力于民族弓弦乐器形制的统一、音色的改进等改革,贡献良多。特别是他赋予板胡、中胡这两种传统戏曲中的伴奏乐器以崭新的生命和表现力,使其登上独奏舞台。
2‘演奏风格的树立。五十年代,民族器乐的演秦尚处襁褓阶段,历史的变革(新中国成立)令文化各层面之衔接措手不及。在此背景下,刘氏以其崭新的形式和内容,清新而又充满勃勃生机的演奏风格亮相,对沉寂的音乐界,自然有着不同凡响的震荡和冲击。他的演奏风格是个性与时代、社会结合的典型,对中国社会及乐界有着巨大而广泛的影响。1957年刘氏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间乐器演奏比赛,曾获金质奖章。
3 优秀作品的流传。刘氏一生创作、改编了大量作品。其代表作如逢年过节在香港也必能听到的《喜洋洋》《幸福年》(民族管弦乐)、独奏曲〈河南小曲〉(二胡独奏)、<草原上>、《牧民归来》(中胡独奏曲)《月芽五更》〈马车在田野上奔驰》(板胡独奏曲)等。由于他的作品具有时代精神,生动表达出人们(或他自己)内心的纯真而质朴的情感,加之其作品吸取了民间传统之精髓,很富于浓郁芬芳之民族色彩,故能引发人们心灵深处的共鸣。这就是刘氏作品风靡流行、历久不衰而又雅俗共赏之原因。
4、诲人不倦的教导。刘氏的演奏风采和艺术成就所引起的社会关注表现在五十年代后期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各大音乐院校已相继开设了板胡专业课程。数十年来,刘氏的学生、弟子几乎遍布大陆各地。近十年,更不乏有大批港澳及海外学生慕名求教。1982年刘氏调入中国音乐学院,将主要精力由演奏转至教学。1985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刘氏与李恒编著的(板胡基本功训练》一书,一定程度上亦代表了他多年来教学上的心得与成果。概言之,刘氏在中国音乐(尤其是胡琴演奏艺术)的薪传承继上所付出的心血及努力功不可没。
上述为刘明源先生生平简历及其主要成就与贡献,在评论其演奏风格时,不可不具备以上粗略的了解(土文中之资料来源于刘氏追悼会上所派发之《刘明源先生生平》,特此说明)。
纭纭中乐前辈中,我最钦佩、崇拜刘明源先生。钦佩其艺术才能,崇拜其天赋资质。他是我艺术上的偶象之一。我与刘先生的交往不算多,亦不算深。22年前我与他同住北京月坛北街。我住17栋,刘先生住5栋(直至去世,此地现已成其故居遗址),还记得我首次冒昧登门求教的情景。刘先生的热诚、谦和及爽朗风趣使我感到如浴春风般亲切,令不善交际、鲜于应酬的我在离京赴港前的那段日子竟不时上刘家‘串门儿”。然严格说来,我跟刘先生仅只上过一、两次课。赴港后亦有书信往来。但我自认对刘先生音乐的了解多过其本人,或可说刘先生的音乐加深了我对其人的了解。我演奏过他的绝大部分代表作,而这些曲目的掌握几乎全部都是根据他的唱片或录音自学的。练秦腔牌子曲是我记忆中最艰辛的一首,听烂了两个卡带(由此可见本人学习上之愚笨,同样情形,刘氏或许三、五遍已足够。然我并不嫌恶自己这种愚笨,因为这就象赛跑的乌龟,虽慢,但却一步留下了一个脚印,代表着起契而不舍的精神)这种学习方法是我在港初期的唯一方法,也是无可选择的不得已之办法。好处是更多地运用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不断地验证和对比自己的学习成果,印象更为深刻。通过这种学习,我对刘氏之音乐风格才有更细致的了解,更深入的体识,似乎令我更加接近刘氏音乐之真谛,激发我探索其奥妙之勇气与信心。
风格的产生即意味着艺术的创造。刘氏的演奏风格,正是他运用其天赋才华以民族的传统精神,配合时代节奏之律动,创造性地展示其个性之典型模式。谈到演赛风格,令我想起在不少年轻人,甚至尚未出道(或刚出道)的学生的简介中常看到“已融汇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有的更加上独特的)演奏风格……”等字样。看后叫人啼笑皆非,为之惭愧。这种现象固然可归罪现代商业宣传之弊端,然亦不无表现其艺术上之浅薄无知。须知在艺术上真正建立起自己独树一帜之风格岂是谈何容易之事。有的人某曲(或某几曲)的演奏自认达到或超越其师(或某名家)的演赛及唱片之水准,便以为可立派树格了。其实为数不少的这类年轻人,其艺术境界与修涵仍滞留在早期的摹仿阶段(这与传统的“口传心授”教学方式有极大关系),然并不自知,反为满足。这就像一幅哪怕比真品更为精细的临摹画作,充其量也仅属赝品而已,谈不上艺术创造。白石老人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足可作为后人艺海迷途之告诫。另一种倾向则是忽略甚至放弃音乐实质内涵的表现,一味追求所谓技巧上的‘突破”(实际上多为较肤浅的表现技法,包括一些极尽视听之娱之雕虫小技),以及形式上的翻新(殊不知那些层出不穷的‘噱头”已令其沦为形式主义之奴隶)。却以此为风格的追求,此乃对风格的误解和歪曲。
我认为演奏风格之建立,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艺术家出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其强烈的精神个性与表达欲望的驱使下,溶汇创新与其个性相宜之技法(这些因人而异的技法往往源自演奏家不同的个性与生理条件,这在胡琴演奏上十分明显而普遍),从而创造出与众不同之音乐形象。因此,真正可以称得上具有独特演奏风格(姑且不论其演奏风格如何)、又具代表性的二胡演奏家,我认为只有阿炳(刘天华先生在二胡演奏上似乎尚未达到建立风格之圆熟阶段)、蒋风之、张锐、闽惠芬、王国憧。胡琴(以板胡为代表)唯刘氏一人而已。
固然各人其风格未必人人尽皆苟同音乐表达的方式与其深度,演奏技巧的全面与其精深之差异亦属必然之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建立起个人风格的演奏家在某一历史时期(长短不一,视其演奏家之才能,修涵及创造力之高低而定)必定是纭纭名家之中出类拔草者。另一重要标志则是各风格必有以已风格为版本之代表曲目,如刘氏之〈大起板〉〈秦腔牌子曲〉,闽惠芬之《江河水》。蒋风之的〈汉宫秋月》、阿炳的〈二泉映月》、王国憧的〈三门峡畅想曲》〈怀乡曲〉。故此,树立个人独特之演奏风格实非朝暮可就、人皆能为之事。
本人从不以为自己在音乐表现方面乃至技法上能够开创出一个新的——即有别于众家、而更重要的是又适合自己、并又能令自己满意的风格。如此说绝非谦逊。事实上,人们(包括我自己)的演奏不同程度上都具备其风格,只不过是别人的而非自己的、或部分是别人的而不完全是自己的罢了。
刘氏演奏所表现的风采气质、隽逸神韵,精深技艺与广吐博纳之大师风范,实可谓前无古人,当今乐坛亦难逢其匹。刘氏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西乐的基础更谈不上深厚。其成功之奥秘在于他真正立足扎根于传统;并能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大海洋中广纳巧取,达至博厚之蕴蓄,方可系北腔南韵之精华于一身;集各派所长之大成为已者。另一十分重要的因素乃是极为丰富的演奏经历为刘氏提供了宝贵而充分的艺术实践:仅是为一千部影片录音之乐历已令人望而兴叹;而刘氏长年活跃于舞台所特有的熠熠光辉更为人们所熟悉。对于我们演奏家来说,舞台就是生命。所谓‘实践乃成功之母”,刘氏之演奏风格正是他大量艺术实践经过总结、提炼而升华之艺术结晶。
我以十六字概括刘氏演奏之风格特点:达旷清芬浓丽精妙;恣肆洒脱、意趣隽永。
刘氏演奏风格中即有豁朗旷达之北国豪情,亦具清新芬芳之南国气韵。其中固然源其绝佳的艺术天赋 — 对音乐具备极之灵锐的反应和颖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具有超人之“乐感”),然更重要的乃是出自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及其心灵深切之感召和颖悟通过激情的宣泄所引发之艺术创造力。此创造力表现在刘氏于传统音乐中博广汲取并巧妙地采读纳集而自成风格,故在他的演奏中不但可以感受到高迈豪壮、淳厚朴拙的北国气质甚至也可令我们呼吸到一丝丝江南丝竹或广东音乐所特有的清芬气息。其细腻精妙之艺术处理中亦可隐约见到蒋派风格潇洒浓丽的痕迹。刘氏制作的两首著名的中胡独奏曲(草原上沟(牧民归来》,无论从作品或是演奏上分析,均不失为具独创性的杰出代表作。
中国传统美学讲求意境,音乐上即韵味(亦所谓的“空间美感’),在民间称其为“神韵”。“神韵”来自演奏家超绝之技艺与深遂的情思相溶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琴合一”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刘氏具有捕捉乐曲灵感和神韵之禀赋,运用这种禀赋之差异乃是大师与匠人之别:大师可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匠人却视而不见或浅肤滥用做刘氏演奏的〈大姑娘美》、《草原上》、《月芽五更》等乐曲清新灵秀、涵摄神韵;意趣纵横而回荡心旌。
在演奏上韵味除了代表意境之外,还有一重要内容:乐曲与人一样,不仅有名字,还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特征,简言之韵味即乐曲之风格。只有喑熟并掌握其风格,才有可能表现出乐曲的面貌及内涵。这方面刘氏显示了卓越的才华,各地的音乐风格,他均具有惊人的准确而概括的洞悉和表现力。其创作并演奏《河南小曲便是鲜活的例子。
所有作品中,我认为刘氏演奏的《大起极》(何彬等编曲),是其个性精神及演奏风格最突出之代表。刘氏演奏此曲时年方二十有余,在短短两分钟的乐曲里,我们可深深地感受到刘氏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充满生机的活力,朝气蓬勃的热忱和对事业前途满怀憧憬的鼓舞。颇具龙腾虎跃之势的〈大起板〉一曲,象征了五十年代中国音乐的振兴,亦显示了时代社会的精神风貌。刘氏以恣肆奔放之演奏冲破了传统音乐的束缚与羁绊,就此建立起崭新的音乐风格。
刘氏之演奏技法无疑也是他独特风格的一部份。叫人甚为羡慕的乃是演奏方法的极为松驰(刘氏得天独厚生有演奏弦乐器最佳的粗大而多肉的手指),令其音色清透明澈、圆润华兹,至今无出其右者。刘氏的演奏技巧,正是因为建立在极为松驰的演奏方法之基础上,故能获得全面而持久之保证。刘氏音乐所富有的生动、活跃、灵巧而富变化特色也是其演奏风格的一大特征。
中国民间传统在演奏上讲究“活”、“巧”而忌“板”。‘泊”。刘氏自幼饱浸中国民间与戏曲音乐,受益匪浅,影响至深。他的揉弦与装饰音的运用以及运弓的多端变化,均取自民间,然又细致、高明于民间,堪称一绝。此外,他的演奏从不拘泥于固定的诠释格局,常随心绪灵感而变化,故次次不同,给人以无穷新意。因此,仅从乐谱上要学到他的演奏是极困难的(这也是我学“秦腔”为何听烂两个卡带之原因)。高胡名家余其伟演秦的传统广东音乐,亦具相似之处,可谓达到了‘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的境界。在这方面,余其伟与刘氏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世无完人,艺无止境。刘氏光辉的艺术生涯亦有令人婉惜的局限与遗憾,为了艺术的探讨,在此大胆一抒己见,不敢妄自批评。
以刘氏之天赋与能力,并具中国音乐深厚之蕴蓄及对各类胡琴精深之驾驭,断不应只留下这批屈手可数的代表作。刘氏后期的录音作品,大多为早期曲目的重复,新作似仅有近年龙音出版的刘氏专辑中之大型板胡协奏曲《春、夏、秋、冬》(四乐章),然并不理想,无论作品或演奏均不能代表刘氏水准,更谈不上发展创新。
刘氏少年得志,早期成名,荣誉赞美无形中束缚了他的奋斗精神与创造力。在乐坛享有的崇高地位,加上中国传统过于看重的派别门户之见,相信极大程度地约束了他主动地广泛涉猎其它曲目。刘氏艺术上的辉煌时期是五、六十年代,此后再无可与此比美之高峰。另一方面,以往那种论资排辈、无可竞争、保护权威之制度同样无形中制约了刘氏艺术上的能量与活力。加上刘氏持其过人之天赋,满足于所取得之成就(至少客观上如此),艺术上逐渐缺乏主动进取之精神。曾听不少人说过,刘氏极少练琴,就是演出前亦难一见,老实说我心里十分羡慕。如果极少练琴之流传属实(以刘氏之天份和能力,仅应付其保留曲目,疏于练习之说应该可信),那么刘氏未能更广泛开拓其曲目便又多了一个理由。
刘氏演奏上的另一个局限和遗憾乃是在上述背景下,刘氏不曾或缺乏累积演奏(包括创作)大型胡琴作品(协奏曲)之经验。正因如此,其晚期之唯一大型作品《春、夏、秋。冬〉才未如理想。本人绝无褒“大”贬‘小”之意(传世佳作、何有大小之分?端在艺术精神之体现)。然演奏大型作品,在音乐的表达上(包括技巧)以至观众的感受上均具备更大更多的纵深余地。成功的大型作品,或以电烁雷霆之凌厉气势,创造出雄伟壮丽的音乐奇观;或以悲怆沉痛之深刻残酷展示出人类灵魂之深切共鸣,其艺术之魅力震摄魂魄、摇撼心挂、摧捣肺腑。放大型作品的演奏,需要演奏家在其个性上与艺术观念上具有更大之包容。“协奏曲”这种演奏形式以胡琴为主角早在六十年代初已面世(中胡协奏曲(苏武)----刘诛曲),七十年代后期已渐为普及。而刘氏身为一代宗师,却未能在胡琴现代发展领域之重要表现形式(协奏曲)中具有人们期望中的表现,实为一大遗憾。
刘氏演奏的作品大都旋律清新、风格浓郁、精致小巧。玲珠光彩,放具雅俗共赏之效。但通常雅俗共赏之作品(一般而论,并非绝对)却较欠缺深刻之内涵或深速之意境。固然乐器性格之差别与乐曲内容之通异极大程度左右甚至决定其乐曲表现之意境深度。然无可否认,演奏家个性的导向与艺术观的追求对其音乐表现有着直接而关键的影响。从刘氏一生演奏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此一令人惋惜之局限。
诚然,对于刘氏大师以上之分析似乎近于苛求,然确是我等后学所寄于之末能实现的热忱期望。
刘明源老师除了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和他醉人的音乐之外,还给我留下了两件永世珍贵的纪念。一是1978年他将出国演奏曾用的一把中音板胡赠送于我。二乃1987年,我为台湾福茂唱片公司赴大陆制作一批中乐唱片。首要人选之考虑,自然是为刘先生出版专辑。想不到此专辑现已成为绝响,成为我永久的纪念和缅怀。黄安源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先后师事聂靖宇、蓝玉崧等名师。曾在北京中国京剧团和中国铁路文工团担任二胡、板胡独奏及中乐队首席。1977年迁居香港,现任香港中乐团团长兼助理指挥。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常务理事、国际名人传记协会终生会员,并任教于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
|
| |
| 编辑:国际艺术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