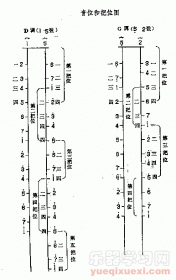为什么说教学是演奏的前期准备和积累阶段呢?因为演奏阶段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技巧,所必须了解的发音状态,所涉及的有关知识,绝大部分要在教学中完成。这个阶段的各种积累实际上是在为演奏铺设一条通达之路。这条路铺不好,演奏过程必然是坎坷的,甚至无法达到演奏的终点站(不能完整的解释作品)。教学过程为什么又是发现和培养演奏家的过程呢?因为一个演奏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演奏家个性、才能、气质可能早已表现出来了,教学过程中,如果及时发现了这些,并且及时的引导、培养,那么一个演奏家可能就顺利的诞生了。相反教学过程中扼杀了或压抑了这些,一朵本来可以绽开的演奏家之花在没来得及绽放时,可能就渐渐的枯萎了。也许有人说:是黄金总会闪光的。这话针对黄金也许是真理。黄金在被埋没了许多世纪以后,一但被开采出来,就会闪光。但这句话对人来说不是真理。一个人被埋没一个世纪,他的生命已经划上了句号!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所有潜质也都永远的消失了。可见,教学过程对于一个演奏家有多么重要!
为了更好的论证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段话:“应该尽可能多地听伟大的小提琴家的演奏,而尽可能少的和他们中的人学琴。”(卡尔•弗莱什《小提琴演奏艺术》第二卷35页) 这里的提法听起来不可思议。一般的看法是:能向那些伟大的演奏家学琴是梦寐以求的事,而这里的提法却是尽可少地跟他们学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要多听而少跟他们学呢?
毫无疑问,能够称得上伟大演奏家的演奏必定是独具个性的。他们的演奏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他们只是复制了任何一位前人的经典“产品”,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演奏家。多听他们的演奏,他们发音的典范,对作品的诠释,鲜明的艺术个性无不使人感到惊叹。惊叹之余就如一个曾经“营养不良”的孩子遇到了丰盛的“午餐”,难免饱食一顿。如果这样的“午餐”消化的多了,那也就不再“营养不良”了。这就是要多听伟大的演奏家演奏的原因吧。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也无庸讳言,一些伟大的演奏家在教学中的表现就很难说是伟大了,概括的说:伟大的演奏家所提供的教学往往是“只能这样演奏,不能那样演奏”;或者“我拉你看”;或者“你跟着我拉”。甚至有些演奏家在教学中简短的几句话就把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伤透了,甚至发脾气骂学生。学生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性的机器,必须按他们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他们希望学生成为他们的第二,而结果学生最多是他们的“复制品”。实际上,如果一个演奏家都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模式来要求别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只能剩下他一个演奏家,别人永远不能成为演奏家,因为别人只能都是“复制品”。这就是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如果一个学生总是不能把自己的演奏置于整个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演奏时他的身后总是立着一个标签式的影子——他的老师,那么他还能成为演奏家吗?
对于上述的教学形式,卡尔•弗莱什批评道:“用‘我拉给你看’的方式教琴方法教出来的学生最多只能是机械的模仿者。他永远不会发展自己的个性。”(《小提琴演奏艺术》第二卷341页) 又说:“‘好发脾气者’、‘自我中心’、‘自觉是独奏者’诸如此类人物不适合当老师。”看来对一个教育家的要求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那么教学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初学时不要走样,基础学好了,有了基本功就要培养个性;高级阶段就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几句话微言大义,能说的容易,会做的不多。
“初学不走样”,实际就是老师确立正确的演奏方法、练习过程以后,要求学生高标准的做到。这个过程是少不了示范的,而这个过程的示范必须要求学生不走样。因为这个阶段是在为一个演奏家的成长创造基础条件。这个阶段走样了,一个演奏家可能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继而,一个好的老师必须能够在教学中提供发音的典范,并且逐渐从示范中走出来。充分发现学生的个性,哪怕就是灵光一现,也能够善于抓住。我们在观察张锐、张韶、蒋巽风的教学时,经常听到他们对学生说:“你的这一句处理的很好!”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甚至会在自己的演奏谱上标上:某某是这样处理的。其实那哪能算得上是处理,也就是灵光一现而已。但是老师的这一欣赏正如贝多芬的一吻,谁能估量这一欣赏,这一吻,对于一个演奏者来说具有多大的价值呢?到了学习的高级阶段,学生成为演奏家的基础条件都具备了,老师的任务则主要在于发现、培养、发展个性。让学生学会如何把手段和表现结合起来。因此,这个阶段需要的不光是演奏家,更需要真正的教育家。张韶、蒋巽风、安如砺都是蒋风之先生的传人。他们的演奏都有蒋派的典雅和古朴,但他们又各具个性。张韶人文;蒋巽风传神;安如砺委婉。但他们又都不是蒋风之第二,这正是蒋风之先生教学的成功。
卡尔•弗莱什批评了上述几种教学者之后,又提出了几种成功的老师:一是基础型老师。这类老师能引导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训练过硬的基本功;二是示范型老师。这类老师能够提供发音的典范。发音的典范并非是示范某首乐曲,或某个片段,而是要提供适应表现各种情绪的声音;三是艺术型老师。这类老师兼有前二者的特点,同时能帮助学生建造起艺术的大厦。这大概也就是人们称道的教育家了吧。当然在这个阶段“学生应该学会依靠自己,学会合乎逻辑的思考问题和找出并满足自己在艺术上的需要。这样他最后就会具备充当那个其责任是对他的发展以最持久影响的教师的条件——这个教师就是他本人”(同上,357页)。
本节前文说过,教学的“产品”不都是演奏家。作为教者,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时时保持清醒的认识,分清卡尔•弗莱什所概括的四类学生:一、“先天独具个性,天生就是‘独奏艺术家’”;二、“分析才能占主导地位,因而更适合做老师”;三、“一般才能——乐队的后备力量”;四、“业余爱好者”。这样在教学过程中便可因材施教,各得其所。
音乐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能否唤醒听众由于生活的积累而潜在的、本来就储存在大脑之中的、暂时蛰伏的情感,从而引起共鸣。人的个性是两重性的。一是人的绝对个性,这是与身俱来的,其特征是其具有稳定性;一是人的相对个性,是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教育所造成的,它的特征是具有不稳定性。由于这种不稳定性造成人的情感的复杂性。俗话说:人到上百,五颜六色,这不仅是指人的外在形态,主要是指人的内在感情的多样性。听众欣赏音乐的过程,就像在花园里赏花,他们要求看到百花争艳,以满足相对个性的要求。如果花园里只有一种颜色的花,可想而知会有多少欣赏者。
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应该是培育不同品种的花草树木的过程,音乐教学的终极应该是让音乐的花园里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从而引起人们对美的愉悦。
发展论
论点:“小提琴在学科发展方面的系统性、完善性为二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范例,二胡应该借鉴小提琴,但这只是一种途径,而不是目的。二胡的发展必须在不丢失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从中西结合中打出一条新路’。” ——蒋巽风
近百年来,二胡艺术得到了比较充足发展。在民乐当中,二胡的发展显然占优势地位。纵观二胡的发展之路,虽然坎坎坷坷,但大体还是遵循了刘天华先生的“从中西结合中打出一条新路”的发展观。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思考:一是所谓坎坷是什么意思?二是怎么在中西结合中打出一条新路?
所谓坎坎坷坷,是说二胡乃至整个民乐的发展总是在摇摆过程中艰难前行。早在刘天华时代,看不起民乐,贬低民乐的大有人在。刘天华先生在《月夜》及《除夜小唱》的说明中说:“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从刘天华先生这段话中,可以想象出当时有些人对二胡的贬低程度。对此刘天华先生给予了批判。他接着说:“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的粗鄙与文雅,主要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其实天华先生的这个观点当是不难理解的,何况当时贬低二胡的“有人”当中不乏音乐名家,何能认识不到音乐的“粗鄙淫荡”难道与二胡这件乐器有必然的联系吗?可见这个时期二胡在媚外的气氛中向前发展有多么艰难。但经天华先生的努力,二胡总是发展起来了。
1963年“上海之春”的二胡比赛是二胡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这次比赛不仅推出了一批优秀人才,还产生了许多优秀曲目,二胡的发展呈现出的良好势头。可是随之而来的“文革”期间,又是另一种情形,虽然没有媚外,但是许多优秀的传统曲目同时受到了冷遇,甚至连刘天华先生的十大名曲也很少听到,经常听到的总是那么几首乐曲。1963年“上海之春”的发展势头又停滞下来了。
“文革”后期,二胡的发展又艰难起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二胡逐渐进入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刘文金、闵惠芬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长城随想》将二胡的发展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八十年代末至近几年,二胡的发展却大有小提琴化的势头,特别是在一些高等音乐学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二胡演奏传统曲目似乎不屑一顾。一些学生演奏起传统曲目平淡如水。大量的小提琴作品被移植到二胡中来。国内一些作曲家也尝试着作一些耳目一新的乐曲。然而这段时期的二胡发展却又不能简单的用“媚外”来下定义,因为小提琴曲移植到二胡中来使二胡的技术、技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几乎到了极限。王建民先生的作品拓宽了二胡曲的创作思路。当《长城随想》把二胡曲的创作推向高峰时,王建民的创作体系可以说是另辟了一条新路,当然在这方面从发展到成熟同样需要过程。但是问题在于,二胡目前从演奏到创作是否又有丢弃传统的危险呢?这倒是另人担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