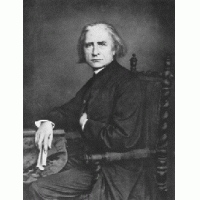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原因
西欧音乐体系中,既有单声部音乐,也有多声部音乐,但具有典型意义并标志着音乐艺术化发展的是多声织体结构。西欧多声织体结构先后经历了两种类型:一是复调织体结构,这种结构的音乐称为复调音乐(polyphony)。复调音乐是建立在横向旋律的线性思维基础上,将具有独立意义的多层旋律线同时结合而形成,其创造过程一般是在一个现成旋律声部的基础上添加其他声部而成,而处理各声部纵向关系的手法主要是“对位法”(counterpoint),即音对音的手法。西欧复调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在10-18世纪。二是主调织体结构,即以一个旋律声部为主,其他声部以陪衬、烘托主要声部的方式出现,这种结构的音乐称为主调音乐(homophony)。主调音乐是建立在纵向立体化思维基础上,将表现音乐内容的重要功能赋予主要旋律声部,其创作手法主要是“和声”(harmony),即和弦构成及和弦连接的方法。主调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在17-19世纪。从复调织体到主调织体的发展既是西欧音乐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音乐的主要特征,也是西欧音乐艺术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与西欧乐系比较,中国乐系的织体结构以单声织体为主体,具有横向织体思维的特点。中国音乐的单声织体结构与横向思维并不是第二个千年特有的产物,而是第一个千年的延续发展。国内学术界将19世纪以前的中国音乐统称为“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四个维度构成。[⑩]无论哪类传统音乐,留存下来的作品大多都是单声部的。这种音乐作品只有一个旋律声部,旋律是作品的“灵魂”,离开了旋律音乐很难存在与流传。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集整理的《中国民歌集成》、《中国说唱集成》、《中国戏曲集成》、《中国歌舞集成》、《中国器乐集成》中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单声部的。这些音乐在实际表演中,不同的声音或乐器也可能作一些即兴式的简单的多声处理(主要是你繁我简、你高我低、你弹我拉、你上我下等手法)使音响丰满有厚度和层次感,但这种多声都是围绕主旋律而展开的,并不像西欧的多声部音乐那样,既不是复调对位的声部结合,也不是按照和声的逻辑功能结合而成的声部结合。
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多声部音乐。如在蒙古族草原上,就有一种专用于在庆典上歌颂领袖的歌曲,是多声部的。通常这种歌曲由两人演唱,一位唱旋律,另一位用一种特殊的浑浊嗓音从头至尾只哼一个保持音,中间惟一发生的变化是在浑浊的声音继续进行的同时,又重叠上一个与之有着十五度之差的高音(用一个嗓子发出两个音是蒙古族歌手的一个绝活,被称为“呼麦”)。中央音乐学院的钱茸认为,“后者的演唱效果极像藏族圣殿布达拉宫外面那一排喇嘛吹奏的声音,产生了威严而居高临下的震慑力,这声音与主旋律声部似乎毫无音乐的内在关系,仅仅是一个混沌、狞厉的权势背景。”[11]这种多声部音乐与西欧的复调音乐相比,它实际只有一个旋律声部,另一个声部的旋律性很弱,仅仅是一个背景。而西欧大多数的复调音乐,各声部并没有主次之分,切相对独立,各声部纵向结合时也注重音的谐和性。此外,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如侗、壮、瑶、布衣等族都有多声部歌曲。其特点是,以主旋律为基础,不时出现一些交叉旋律,但很快又回到主旋律上,每个乐句的结束音几乎相同。这种所谓的多声部,实际只有一个主旋律声部,而其它声部是主旋律声部的变化或补充,并不是独立乐思的声部,也不与主旋律声部从主题思想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手法主要是变奏和模仿。这种多声部音乐与西欧的复调音乐或主调音乐有着很大或根本的差别。
三、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缘由
为什么中国音乐在千余年的发展中以单声部织体结构为主,而西欧音乐则在第二个千年中形成了以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为标志的多声部音乐?可能影响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很多,但社会结构的不同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下面仅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社会原因。
1、社会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关系
音乐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结构而言,音乐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子结构,音乐结构与社会结构是整体与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音乐结构而言,社会结构是音乐结构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所谓结构的“转换性”,也就是意味着结构的表层和深层是一个可以转换的整体,这种转换使得音乐结构与社会结构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制约音乐结构的形成与变化。“整体性”是结构主义的特征之一,即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内时的性质。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整体及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就人类社会的变迁而言,社会结构在历史长河中是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结构是不完全相同的。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社会结构可称为历时性社会结构或社会的历史结构。历时性社会结构理论是由当代史学大师、法国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12]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结构或历时性社会结构。按照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可将社会的历史结构或历时性结构分为表、中、深三个层面:
表层:突发的社会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
中层:一定时期内变化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生产的增减等。
深层: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
这里的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正是本文所说的社会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它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对社会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它通过其文化属性的相对稳定性和统一性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发展,音乐文化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音乐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通过文化内涵进行转换。无论社会结构还是音乐结构都是社会文化的结果,它们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同时又必须通过主观的探知才能认识,它们都有其文化内涵,通过文化内涵,它们之间实现了转换。在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家那里,社会制度组成了一个社会的框架或骨架,制度结构是由社会共有的“规范”所建构。而这种规范就是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作为一个社区或社会的一员所共有的。它们存在于人的头脑里,包括人们所共有的信仰、思想、情感和符号等。正是这种文化给人们提供了行动准则、行为规范、合法信仰。这种文化通过交流可以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并且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被社会的新成员(婴幼儿和小孩童)所接受。帕森斯认为,社会制度是“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那些明确什么是感觉上人们行动或社会关系的恰当、合法、期望方式的规范化模式。”[13]因此,制度结构既是一个概念化的客观实在,更是一种社会共有的主观文化;它既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又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各类实践活动中。音乐是社会文化的一个范畴,社会结构的文化属性也必然反映到音乐文化上。人们创作音乐、听赏音乐的思维模式不仅是音乐的结构模式,同时也是社会成员哲学思维的结构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与社会结构的文化属性相一致的。
前述音乐结构也有表层、中层、深层三个层面构成,其中深层意义化的精神内涵则是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共有的文化,它既体现在音乐中,又体现在所有文化现象中。这里的精神内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作为一个社区或社会的一员所共有的。它们与社会结构的文化属性是共同的,存在于社会成员的头脑里,包括人们所共有的信仰、思想、观念、情感和符号等。正是音乐结构与社会结构文化内涵的共同性,音乐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实现了转换,社会结构可转换为音乐结构,音乐结构可转换或体现社会结构。
上一篇:陕西交响音乐创作发展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