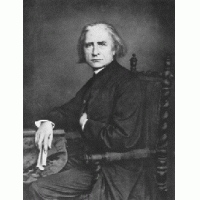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原因
2、多元社会结构催生多声织体结构
多元社会结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它形成于中古时期,其形态主要表现为二元权力体系、多元权力主体和多元法律体系等。西欧前现代社会的多元社会结构特征可概括为一二三:
一是社会结构围绕一个权利观念,即主体权利观念而建构,正是主体权利的不断实践与发展,中古西欧产生了与王权抗衡或制约王权的社会力量,形成了权力制衡的社会结构。
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社会结构有两大权力体系支撑,以教皇为代表的教权体系与以国王为代表的王权体系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内部并发挥作用,它们之间既有对抗与制约,也存在合作与利用。另一方面,尽管西欧中古社会存在着多元的社会主体,各社会主体也都有相应的权利,但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二元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既紧张对立又合作利用的关系,当二元主体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双方主要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而非取代或推翻对方的角度出发,采取谈判、法庭斗争、货币赎买、甚至是战争和战争威胁等手段,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建立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有三层含义:一是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在三个社会主体群(贵族、教士、市民或农民)上建构;二是中世纪的社会权力主要由贵族、教会和第三等级三方控制;三是西欧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三大传统,即日耳曼传统、罗马法遗迹和基督教思想。
上述特征既是对西欧多元社会结构显性框架的一种归纳,同时也是对社会结构隐性文化属性的提炼。这些特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西欧的其他文化一样,深深浸透于西欧人的思想意识中,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反应在音乐上,那就是催生了多声部的音乐结构。
西欧音乐织体结构的形成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具有惊人的同步性。
9、10世纪,是西欧复调织体结构兴起的时期,典型的代表是“奥尔加农”(organum)。这种复调织体只有两个平行四或五度的声部,上方声部是基督教会在礼拜仪式中的一种吟诵式的“圣咏”,下方声部是新添加的,两声部在纵向关系上体现出一种协和、稳定的关系。在社会结构方面,这时期也正是二元权力体系形成的初期,教权体系与王权体系更多的也是相互合作与利用,还未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与制衡。
11、12世纪,复调织体结构的声部数量仍然以二声部为主,但由于两个声部都注重横向旋律的独立性使得两声部间纵向的不和谐因素增多;新添加的声部更多出现在上方声部并具有流动性和富于变化的装饰性性格,而圣咏则处于下声部并且节奏缓慢、旋律性减弱,似乎成为辅助性或陪伴声部。在社会结构方面,这时期正是教权与王权发生冲突或碰撞的时期,典型的例子是“教皇革命”,即11、12世纪期间,教皇与王权之间为争夺主教授职权引发的教会与世俗权力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其结果是教权与王权双方谁也没有被谁吃掉或取代,而是达成一种妥协,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14]
13-16世纪,是西欧复调织体结构大发展的时期,复调织体在声部数量上是以三声部为主的多声部构成;各声部在横向上继续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在纵向关系上追求声部间的和谐与平衡。在社会结构方面,这期间是以教皇、国王、贵族和市民代表构成的多元权力主体的抗衡与制约、共存与合作为主要特点。法国在1302年召开的有教土、贵族和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继法兰西之后,英国也产生了等级议会,等级会议的第一、第二等级是僧侣的和世俗的贵族,第三等级是非贵族的富裕市民代表。在一个国家内部,主要有国王、贵族(世俗的和僧侣的)和市民代表的三大权力主体。
17-19世纪,多声部织体结构呈现出复调织体成熟衰弱、主调织体兴起发展。复调织体突出的是各声部的独立性,而主调织体突出的是整体结构的协和稳定性。在社会结构方面,这时期多元权力主体仍然存在,但社会公权却逐渐集中于国家或国王,社会公权的集中意味着原来其他权力主体的权力减弱。这期间,教会在世俗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教皇在世俗社会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弱,而这期间的主调音乐大多不用于教会礼拜,也不再依赖教会的圣咏作为创作素材。到19世纪末,无论其基本国体是联邦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或是共和制,大多都采用“三权鼎立”的宪政制度结构,即基于国家宪法下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机构相互分离、相互合作、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这种三权鼎立的宪政制度结构与音乐的主调织体结构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三权鼎立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宪法下的各权力主体的相互合作与制衡,尽管三权分离与制衡,但目的是为了一个宪政制度结构的平衡与和谐;主调织体虽有四个(或更多)声部,但基础是三和弦,且强调和突出一个主旋律声部,其他三个声部是围绕主声部而建立的,整体结构在纵向关系上追求的也是平衡与和谐。
3、单一社会结构滋润单声音乐结构
与西欧相比,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单一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表现形态是中央集权制(或称皇权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没有出现西欧那样与王权相抗衡的教会、贵族、中产阶级等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全部集中于皇权。在这种社会结构下,除皇帝以外的社会各阶层都缺乏主体权利,也难以致富或显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依靠政治特权或接近政治特权而发达外,没有一条与之并行、并受到保障的渠道。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这一结构的概括。
西欧社会的神性与俗性是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的,精神世界的领袖与世俗世界的领袖是分离的,从而形成了政教分离的二元体制。“在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学,而儒家学说并不是官僚皇帝制的对立物,恰恰相反,儒学与后者相伴相生的。”[15]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及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学与皇权官僚的密切联系,使儒学成为皇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及其信徒与皇帝制度是一致的,称为儒生的儒家信徒,是皇帝选官的基本对象,尤其隋唐科举制以后,儒生为皇权所用更加规范化,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军。而中古西欧的基督教会并非只是一个从精神上抚慰人类的宗教组织,它所涉足的权力远远超越了精神抚慰的范围,凡是教民或信徒的诸如生命、财产、婚姻等世俗问题,都是它的权利范围。它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同时又是世俗事务的管理机构,它和各王国的国王、贵族一道共同统治和管理着西欧社会。正是基督教会对国王权力的制约与抗衡,使中古西欧形成了以二元权力体系为中心的多元社会结构,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现代转型。尽管中国也有本土的道教、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等,但从信徒的数量、对社会影响的规模等方面都不能和儒家学说相提并论,更不能成为与皇权相抗衡的社会力量。
中古西欧在二元权力体系下存在着多元的权力主体,主要有教会、国王、地方贵族和中产阶级。各权力主体间形成了一种既有矛盾冲突,更有合作利用的契约关系。当社会主体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双方主要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而非取代或推翻对方的角度出发,采取谈判、法庭斗争、货币赎买、甚至是战争和战争威胁等手段,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建立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中国皇权的统治靠官僚士大夫,官僚士大夫只是皇权统治的工具,并不与皇权发生冲突与对抗,这与西欧国王与贵族的关系,完全不同,同西欧王权与议会的关系更是相去甚远。中国的皇权与官僚,不存在西欧王权与贵族的那种契约性的关系。中国官僚的权力是皇帝封授的,皇帝可以给予,也可以收回。因此官僚只对皇帝负责,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违抗“圣旨”要被贬职、撤职,以至杀头、灭族的危险。所以,官僚在下属、百姓面前,盛气凌人、趾高气扬,但在上属和皇帝面前却顶礼膜拜、卑躬屈膝,缺乏最基本的个人权力。随着皇权专制的延续,官僚士大夫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始终是皇权的一部分,一个附属物,他们既没有独立的权利,更谈不上与皇权抗衡,也不是皇权与贫民之间的中间等级。
上一篇:陕西交响音乐创作发展述评